
年夜饭后,母亲端上来的茶还冒着热气,父亲已经拎出那个褪了色的蓝绒布盒子。它落在玻璃茶几上,“啪”的一声,像一个温和的句号,结束了关于春晚节目的短暂讨论。我知道,一年一度的仪式,就要开始了。
爷爷照例坐在朝东的主位,那是他几十年不变的位置。他用那双爬满深褐色老年斑的手,缓慢而郑重地打开盒盖。没有我们在商场里见过的精美扑克牌盒,只有用旧挂历纸反复包裹的、沉甸甸的一副牌。纸的边缘已磨损起毛,露出里面灰白的纤维,像某种古老经卷的卷边。他将那叠厚重的牌“哗”地倾倒在桌上,声音沉闷,远非新牌那般清脆响亮。
于是,一年中最漫长的沉默降临了。这沉默只属于洗牌时分。
爷爷的洗牌毫无技巧可言,甚至有些笨拙。他无法像电视里的赌神那样,让纸牌在指间奏出流畅的弧线。他只是将整副牌笨重地分成两摞,然后用拇指抵住牌背,让它们艰难地、一片压着一片地交错、咬合。那声音是“唰—啦—唰—啦”的,滞涩,甚至有些刺耳,仿佛能听见纸张边缘相互刮擦的微小痛楚。父亲的眉头会不自觉地微微蹙起,那是他作为工程师对一切不够“顺滑”的事物本能的反应。但他从不开口,只是将目光投向窗外墨蓝色的夜空,那里正零星地炸开几朵烟花。
德州扑克我小时候曾无比憎恶这冗长的前奏。同学的父母都用崭新的扑克,甩在桌上噼啪作响,干脆利落。我曾鼓起勇气买回一副最贵的塑料扑克献给爷爷,他却只笑了笑,第二天,那副泛着化学光泽的新牌便不见了,蓝绒布盒里,依旧是那叠厚厚的、用旧历纸包着的“砖头”。
今年,当那熟悉的“唰啦”声再度响起时,我第一次没有感到焦躁。我仔细地看着爷爷的手——关节粗大,皮肤像被水浸泡过久的宣纸,布满纵横的褶皱与深色的斑点。他的全部精神都贯注在指尖,仿佛不是在洗一副牌,而是在进行一次精密的、不容有失的拼接。我突然明白了,他洗的不是牌,是时光。
这副牌里,一定有某一张的边角,还沾着我三岁时好奇的口水;有另一张的牌面上,留着五年前表姐失手打翻果汁时晕染的淡黄痕迹;或许还有一张,背面那道轻微的划痕,是某一年父亲争论牌局时不慎留下的印记。五十四张牌,就是五十四片时间的切片。爷爷用那双迟缓的手,一遍遍地将这些散落的岁月重新搓揉、整合,让它们在这一夜,暂时变回一个看似完整的圆。
牌终于洗好了。他将它放在桌子中央,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作品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疲惫。
“来,切牌吧。”他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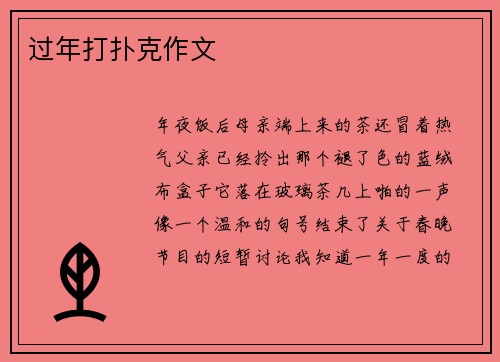
我伸出手,在那叠厚实的、边缘已磨得温润的纸牌上轻轻一按。指尖传来的,不是冰冷的光滑,而是一种蓬松的、带着体温般的柔软。原来,我们每个人能切开的,从来都不是命运,只是这一小段被善意地凝固在此刻的、喧闹而温暖的旧时光。
窗外的鞭炮声陡然密集起来,而在这一方小小的牌桌上,只有纸牌被缓缓抽出的摩挲声。爷爷笑了,眼角的皱纹像极了那副老牌弯曲柔和的弧度。在这辞旧迎新的节点上,我们发现,所谓团圆,不过是愿意陪着最重要的人,一起把那些陈旧而珍贵的声响,一遍遍地,听到未来里去。